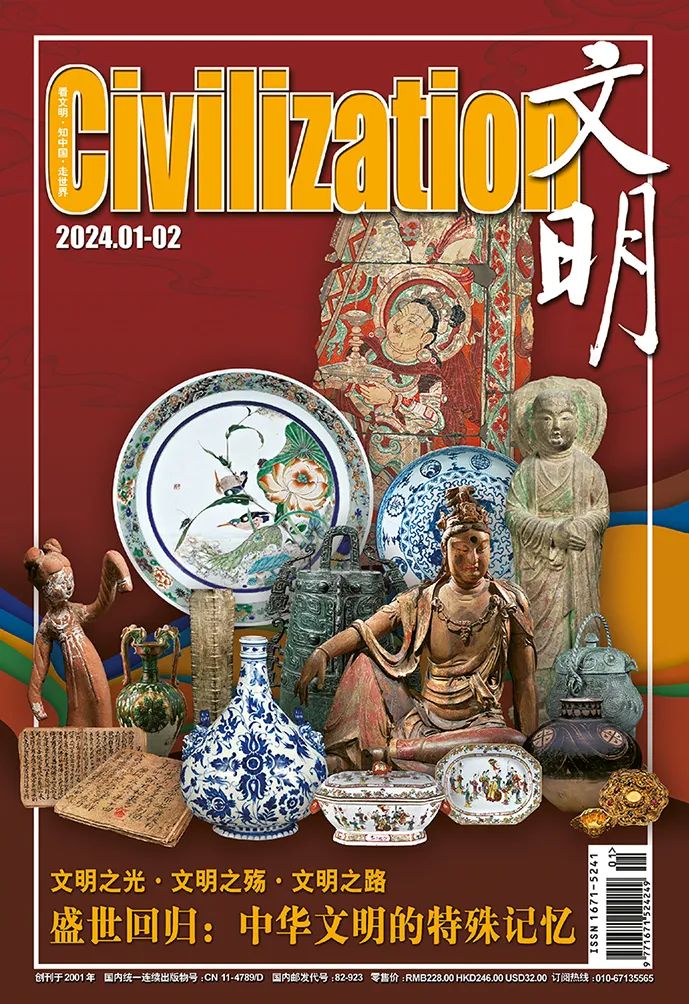引言:
跨越太平洋,是否有幸福的未来
讲述美国的中国收藏之前,首先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感情。多年来,无论亲美,还是反美,两者都缺乏对美国精神的真正认识和全面把握,我们的“美国观”是经过西方世俗化运动、“去基督化”淘洗后的文化遗产。然而,“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守护神”,是无法明白美国的历史的。
美国独立战争在获得政治上的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大英帝国的市场。于是,美国把目光转向太平洋,并在最初的对华贸易中,开始瓷器的定制和捐赠,那些因信仰的缘故拒绝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使他们愿意把当时尚未向外国人开放的领域的物品展示给美国人看,而美国人也在这种“观看”中留下了“美国式直觉”对中国文化最初的指认:“书法大师”与“自我否定”——中美初次相遇时的这份好感与认知,带着各自的缺憾与期翼,形成某种可以照见未来的镜像。遗憾的是,不但这一镜像的意义从未被真正揭示出来,美国收藏中国的道路也没有延续这一脉络往下发展。

19世纪中后期,南北战争和工业革命使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带来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滋生出各种心灵的问题。美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转轨,世俗化逐渐取代基督信仰成为美国精神的主流,当以“波士顿婆罗门”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们试图从“东方智慧”中寻找解决美国心灵问题的方法时,“渴望东方”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瓷器、青铜器、玉器、书画、漆器、家具等成为承受这种“渴望”的载体。
为此,无论是面对商人、学者、外交等不同领域的藏家,还是面对美国收藏中国的众多博物馆,抑或是文物、艺术等不同的收藏品类,我们的重点不在于按图索骥把某一收藏事件或藏品的来龙去脉完全讲述清楚——事实上,由于牵涉诸多复杂因素,任何一个细节上的不同都会使整个收藏事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完全讲清楚是不切实际的——而是想探求美国是否通过收藏中国为他们的心灵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事实证明,偏离了立国之基的美国人,能够欣赏中国艺术之美,却很难理解中国艺术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潜沉,结果是在“收藏中国”的同时“失去了中国”。
通往中国之路:
邓恩的“拒绝”与中国的“好感”
美国人酷爱喝茶。但英国既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又征收茶叶税,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终于导致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船只,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是为“波士顿倾茶事件”,为不久后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独立战争后,带着对远东贸易和财富的渴望,美国商人启程远航,漂洋过海前往中国。
1784年2月22日,由费城富商罗伯特·莫里斯投资的“中国皇后号”商船满载着花旗参、毛皮、羽纱、棉花、铅和胡椒等物,从纽约启航,开往广州黄埔港。顺利地把货物出售后,又满载着茶叶、棉布、丝绸、瓷器等物,原道返回。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驶入纽约港后,船上货品大受欢迎,旋即被抢购一空。可以说,在美国建国一代的认知中,与亚洲的新贸易是这个新生国家自豪感和繁荣的源泉。
受“中国皇后号”成功的激发,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投资或冒险远航,对华贸易热兴起,1790年代以后,在通往广州的漫长航线上,美国商船络绎于途,中美贸易总额很快就超过荷兰、丹麦、法国,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1800年,塞勒姆成为美国最富庶的城市,“驶向富裕东方最遥远的港口”成为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城中的男孩子们“对广州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纽约”。而那些从贸易中受惠的商人们则成为美国最早的百万富翁,其中不少还是“中国迷”,如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

德比称得上是“最早重视中国瓷器珍品”的美国商人之一,曾向中国的瓷器生产商委托定制餐具、茶具、酒碗等物品,后来一款题有“大特克号”和“1786年广州”字样的酒碗被德比的儿子捐赠给塞勒姆的埃塞克斯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799年,是第一家涉及美国与东亚联系的综合性档案馆,收藏了与此相关的文件和大事记,后与东印度海洋协会合并,演变成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拥有130万件藏品,包括一幢从中国一砖一瓦合法搬迁到美国的18世纪徽式住宅——荫余堂。
1805年,因高额利润的诱惑,费城商人威尔科克斯在货物清单中不失时机地添上了土耳其和印度的鸦片,但贵格会信徒内森·邓恩因信仰的缘故拒绝了,这为他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和信任,愿意把一些当时不向外国人开放的领域的东西拿给他看,邓恩的兴趣也明显超出过去外销艺术品和奇珍异宝的范围,渴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为这个目的,1838年,邓恩在费城举办了历时三年的“中国万物展”,将自己数以千计的庞大收藏进行了展示,吸引超过十万人参观,展览图录《万唐人物》卖出约五万册。
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贸易刺激了美国造船业的发展,飞剪船和蒸汽船取代旧式的、靠风力推进的帆船,航速大为提高,使美国商人在激烈的对华贸易竞争中凭借最先运抵市场、抢先出售等优势赢得了更多利润。波士顿也因为更先进的设备,取代塞勒姆成为美国主要的贸易港口。
初识中国特色:
“书 法 大 师” 与 “自 我 否 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除广州外,又开放了宁波、厦门、福州、上海四处通商口岸。1844年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美国人获得了自由进出五个通商口岸的权利。
为纪念《望厦条约》的签订,1845年至1847年,波士顿人在华盛顿大街的万宝路教堂精心筹备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伟大中国博物馆”展,展出了800多件与中国农业、艺术、贸易、风俗习惯有关的物品:场馆的天花板上有热闹的灯笼和舞动的巨龙,场馆内除了瓷器、珐琅、刺绣这些不可或缺的展品,还有身穿“本土服装”、自称“书法大师”的广东人……不知“书法大师”的称呼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但它确确实实抓住了中国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以毛笔为主要创作工具的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通过“提案顿挫”“中锋用笔”和笔墨在粗细、轻重、快慢、浓淡、干湿等手法中的变化,将中国心灵在面对自然、人与世界时的百转千回表达得淋漓尽致,堪称中国灵魂的“软着陆”——以后,美国对中国艺术的收藏就要在这些“胸中沟壑”中进行艰苦卓绝的鉴别与分辨。

参与《望厦条约》签订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老约翰·彼得斯为展览提供了自己收藏的展品,并编写了展览图录。有研究美中两国早期交往历史的美国学者指出,彼得斯参加《望厦条约》签订的目的,是希望“向中国人展示并解释美国艺术及其生产的模型、标本,包括由美国发明家制造的省时、省力的机械设备”,虽然愿望没能在签订条约时达成,但彼得斯没有放弃,回国后将其体现在展览上,证明中国的官员可以成为“波士顿婆罗门”的理想生意伙伴。
转向东方智慧:
费诺罗萨的“唐宋传统”与“汉字寓意”
彼得斯期冀中的“波士顿婆罗门”,是指波士顿的精英阶层。早在美国建国前,清教徒的宗教伦理就在波士顿塑造了一个极端稳定、结构良好的社会,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波士顿拉丁学校和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都是在波士顿创立的——新英格兰地区进入航海时代、成为太平洋东部的商业推动力时,哈佛大学已进入成年。美国独立后,波士顿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际港口之一,当地一些名门家族的后代成为美国社会“世袭”的贵族文化精英,俗称“波士顿婆罗门”。
在他们的慷慨捐助之下,自19世纪中后期起,波士顿文化呈现出繁荣的气象,1870年7月4日,波士顿美术馆创立;1870年至1900年期间,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图书馆得到“波士顿婆罗门”的大量捐助;1875年,来自“波士顿婆罗门”艾略特家族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开始担任哈佛大学首任艺术史教授,费诺罗萨对他的课程相当痴迷。
在此背景下,受以爱默生为代表的一位论教派注重人的精神方面、提倡心灵直觉的超验主义思想影响,“波士顿婆罗门”被东方智慧中的虚无主义、泛神论、人人可以成神的内容所吸引,试图从中寻找应对美国镀金时代(1870年-1900年)精神危机的方法,“渴望东方”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学人前往中国,他们所抱的态度前所未有,充满寓意。在波士顿人当中,东方艺术是一种时尚,他们要使自己的城市充满伟大的收藏。”美国得以立国的基督教文化价值在这种渴望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轨,正如费诺罗萨所言:“西方文明的活力,源于获得知识的方法;东方的力量,则存在于其对目标的了如指掌。”因为“没有目标的方法是盲目”“没有方法的目标是残疾”,所以,东西方需要合一。

1885年,费诺罗萨在日本的三井寺法明院受戒,从基督教改信佛教。1890年,受波士顿美术馆之邀,费诺罗萨返回美国担任该馆的日本美术部首任部长。1894年,费诺罗萨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绘画展——京都大德寺藏中国南宋绘画《五百罗汉图》展。《五百罗汉图》由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明州(今宁波)鄞县惠安院劝募多名供养人发心出资绘制,每幅五位,共计百幅,其中六幅早年佚失,其余部分于15世纪传入日本,辗转多座寺庙后,被丰臣秀吉存于京都大德寺(日本禅宗文化中心之一,与茶道文化渊源亦深),佚失部分由狩野德应于宽永十五年(1638年)补作凑足。
充满波折的是,展览开始前,两幅作品离奇“失踪”。展览结束后,京都大德寺因日本国内对传统的忽视,经济拮据,为筹措修缮资金,把十幅作品卖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教授兼博物馆董事邓曼·沃尔多·罗斯,后来,罗斯把自己购入的那五幅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失踪”的那两幅“失而复得”后被卖给弗利尔(弗利尔美术馆创建人),剩余的八十八幅返回日本后被指定为“国家珍宝”,受到严格保护。

1896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开馆,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寻求亚洲珍宝的另一个划时代事件。晚年,费诺罗萨在《中日艺术源流》一书中,提出了以“线条、浓淡、色彩”三要素为核心的艺术批评方法(线条、浓淡为中国古代绘画最重要的审美要素,色彩乃西方绘画核心本质之一),认为唐宋之后的“文人画”湮灭了中国艺术的伟大传统,至于那些关于“文人画”的品评系统,不过是些不值一提的“蠢话”。这些观点对美国收藏中国的品鉴、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利尔即为其中代表),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中国学者,导致《中日艺术源流》遭到冷淡对待。
费诺罗萨去世后,遗孀将其论述中国汉字的遗稿交给诗人埃兹拉·庞德,经庞德之手编辑后,以《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为题发表,把费诺罗萨认为汉语可以将空间和时间进行自然融合的特点(这是英语无法做到的)传到西方,成为欧洲现代主义诗歌和意象派运动的里程碑。不过,庞德只编辑出了文章的一半,在另外一半没有被编辑的内容中,费诺罗萨希望把中国宇宙学的关键概念更广泛地引入西方诗歌和社会,在艺术中践行“东西方将合二为一”的观念。
在费诺罗萨去世之前,他已经把波士顿、进而扩展至哈佛大学,变成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他敏感捕捉到的中国文字和艺术的审美本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右着美国收藏中国的基调,但因为脱离了基督信仰的精神之源,他折戟于中国绘画的线条上,看不到那条中国线分隔着更多、更深的东西。
交友中国之古:
波士顿美术馆的 “飞龙在天”
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前,波士顿美术馆在费诺罗萨、罗斯等人的支持和捐赠下,成为美国唯一拥有可供观赏和学习的大量亚洲艺术品的场所。
罗斯亦哈佛学子,并培养了不少可塑之才,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史克曼。波士顿美术馆的《文姬归汉图》《历代帝王图》《北齐校书图》等珍品都来自他的捐赠。据统计,罗斯一生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11000件藏品,其中超半数是日本和中国艺术品。

除了捐赠,接续费诺罗萨工作的冈仓天心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每年都会前往中国的北京、洛阳、西安、上海等地搜求中国艺术和文物,在垄断中国艺术品买卖的古董行山中商会和古董商卢芹斋之外,构建起以其外甥早崎幸吉为中心的购买渠道,使美国收藏中国的脚步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
冈仓天心购买了北宋赵佶《摹张萱捣练图》、南宋夏圭《风雨行舟图》,元代王振鹏《姨母育佛图》等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该馆的中国收藏。《摹张萱捣练图》人物衣服上的高古游丝描细劲有力,面部晕染通过三白法呈现的细腻匀洁,虽是北宋画院中人学习古法、摹唐人之本的作品,却巧妙注入了北宋人物画的高度技巧。
1903年,波士顿美术馆“日本美术部”改为“日本中国美术部”。1912年,冈仓天心请中国书画家吴昌硕题写了“与古为徒”(与古人做朋友之意)四字,制成匾额,安放在波士顿美术馆中国部大厅,并附有如下跋语:
波士顿府博物馆藏吾国青铜器及书画甚多,巨观也。好古之心中外一致,由此以推,仁义道德岂有异哉?故摘此四字题之。

冈仓天心之后,约翰·罗吉继任,(传)北宋范宽《雪山楼阁图》和南宋陈容《九龙图卷》等都在其任内购入。罗吉之后,富田幸次郎继任,迎来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收藏扩大规模的黄金时期,入藏有北宋赵令穰《湖庄消夏图》、南宋鲁宗贵《吉祥多子图》等名作,首次出版了馆藏中国古代绘画的完整著录。其中,《九龙图》纯用谙熟的水墨勾、划、点、渲、喷、染,描绘出九条龙在海涛和云层中升潜腾跃、显隐出没的瞬间动态,是古代以龙为题材的绘画中最为珍贵的早期作品,反映了道家信仰和思想的寓意。
中国艺术海洋:
弗利尔、慈禧画像和端方
如果说费诺罗萨是美国收藏中国的理论基础构建者,那么弗利尔则是一位实践者。他于1895年、1907年、1909年、1910年-1911年,先后四次前往中国。不过,由于弗利尔选择的路线都是从美国东部出发,经欧洲、非洲、印度、取道南亚和日本,最后抵达中国,前两次的行程重点还是以欧洲和非洲埃及、印度等地为重点,在中国仅去了香港、广州、上海三地,购买了一些陶瓷和文物。
在弗利尔“沉溺于中国艺术海洋”的那些日子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运动结束后,清廷威信扫地,地方拥兵自重,革命风起云涌,清朝的统治命悬一线。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退还了中国的赔款,用于兴办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图书新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前身)等文教事业,中美关系迎来一段蜜月期。

1902年2月,返回紫禁城的慈禧,一个月内两次召见各国外交使团的公使夫人和女眷。1903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夫人萨拉·康格再次谒见慈禧时,为在当时妖魔化慈禧的舆论环境中,展现一个相对真实的女性慈禧,就通过教会女翻译提出邀请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中文叙述中常称为“柯小姐”)为慈禧画像的提议,没想到竟得到允准。创作完成后,画像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成为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为国家形象的重建而作出的改变之一。
1905年至1906年,清廷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8年)之后,推出立宪运动改革,派出戴鸿慈、端方等大臣前往日本、美国和欧洲考察宪政,寻找可供借鉴的政治改革模式。

在美国芝加哥,听闻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筹建计划时,端方承诺捐赠一座唐代石碑;在纽约,他考察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瓷器和玉器。1908年,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举办的上海中国艺术品展上,汉代陶器展品部分借自端方。同年,在助手的协助下,端方完成了自己的藏品目录整理——《陶斋吉金录》,不但在序言中描述了清代金石学蓬勃发展的情况,而且使用照相平版印刷术复制拓片。
1911年9月,端方被任命为渝汉铁路督办大臣,镇压保路运动。没人能想到,11月,辛亥革命的余波中,端方在旗下新军的哗变中被斩首。家道中落和兵荒马乱中,端方家人被迫出售他的收藏,并为此找到了端方的外籍朋友——福开森。
背负中国情怀:
福开森和他的“中国艺术收藏谱系”
福开森与弗利尔和端方都有交集,彼此既从对方那里汲取、也给予过对方对中国艺术的一腔热血,意识到“文人画”传统在美国对中国艺术阐释中的缺席境况后,他致力于扭转这一局面。
1887年,福开森和家人来到中国履行传教使命,负责在南京组建当地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十年后,1897年11月,福开森接受洋务运动代表之一的盛宣怀之邀,以外籍顾问的身份协助筹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成为晚清洋务派与外籍人士合作的代表。
1901年,福开森被选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行政委员会的一员,随后,逐渐身兼编辑和副主席等职务,不但进行了建筑维护、图书编目等有效管理,而且在学会中点燃了对“艺术品”“工艺品”“图像艺术”的热情。

1902年,福开森被聘为端方的外籍顾问,因为近距离“得”到以端方为代表的清代金石学的精神传承与谱系,他肯定了“文人画”在历史序列中的价值;但由于执迷过深,使他在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搜求文物时,表现出轻信、偏执、无法聆听他人建议等缺点,遭到诟病。
1910年至1911年,弗利尔第四次中国之行中,在上海与福开森有过交往。因为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大都会”)的董事们非常熟悉,弗利尔把福开森介绍给了他们。1912年,清朝灭亡后,福开森返回美国办理事务期间,主动拜访了大都会的董事会副主席罗伯特·福里斯特,开始为大都会展开在中国的文物收购工作。此时,大都会的中国收藏主要是明清瓷器(其中部分是摩根私人藏品),馆藏绘画十件。

福开森致力收集流传有序的名家绘画,但他鉴定真伪的能力不足、深信卖家,过于自负,终究未能实现自己构建的中国绘画收藏图景,但从1910年代至1930年代,福开森参与了美国社会对中国艺术观念认识的转变过程。1915年,福开森出任北洋政府顾问后,定居在北京的一处四合院中,致力于中国艺术和考古学资料的积累。1920年代,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34年,福开森向自己在传教士时代创办的学校——南京大学捐赠了1000件文物。
东亚收藏天堂:
福格艺术博物馆与哈佛燕京学社
1920年代,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在两个层面上给美国的中国收藏带来相关的影响,其一就是馆长助理、美籍犹太人保罗·萨克斯开设的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中第一个与博物馆有关的培训课程——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问题课程,整个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末,萨克斯的博物馆课程声名卓著,成为打开美国上流艺术世界的敲门砖,毕业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美国各州的主要博物馆担任重要职位。
另一方面,博物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兰登·华尔纳通过“对中国极具冒险的突袭”,把敦煌和黑水城等佛教遗址的雕像、绘画移至美国,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成为美国敦煌文物收藏的重镇,其中328窟的唐代半跪式菩萨像成为福格艺术馆的镇馆之宝。1926年,华尔纳的考察游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出版。

1925年,华尔纳带领一个包括文物保护专家、摄影师和外科医生的队伍,第二次踏上敦煌之旅。此行,华尔纳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代表哈佛大学和霍尔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商讨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事宜,受当时普遍的反帝爱国情绪影响,北京大学拒绝了这个邀请,第二次敦煌之行也匆匆结束。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了解到其中曲折后,为燕京大学争取到了合作机会,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
重建中国情境:
史克曼与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庙宇”
从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纳尔逊博物馆)开始,美国收藏中国的地理坐标离开东部沿海平原,向中西部移动。堪萨斯城地处美国中部的铁路枢纽,1929年,当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整个世界时,纳尔逊博物馆筹建委员会成立,翌年动工,经过三年建设,1933年12月开馆。
1930年,华尔纳被聘为该馆的东方艺术顾问,1931年前往中国搜求古物,购买了绘画、石刻、青铜器、陶瓷器等物,之后,在谈判一座清代亲王府的建筑时,因不得不前往日本,华尔纳向董事会推荐了劳伦斯·史克曼,华尔纳找到他时,他正在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支持下在北京学习,在华尔纳的邀请和推荐下,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收藏重任,落在了史克曼肩上。
据回忆,史克曼曾和华尔纳专程到天津向溥仪购买古画。当时,这位逊帝的心思全在一辆新买的汽车上,对画作毫无兴趣,陈淳的《荷花图卷》等几幅明代绘画精品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购入的。

1931年夏之前,史克曼在北京的一家棺材铺里,发现了一架智化寺(明英宗年间权倾一时的宦官王振的家庙,倚皇帝宠幸,该寺的很多建筑规格都有僭越之处,尤其是智化殿和万佛阁顶部的楠木藻井,云龙盘绕,结构精奇)的楠木藻井,当时已被拆掉,准备用于制作棺材。在史克曼的抢救下,避免了埋入黄土的命运。
1932年,卢芹斋向纳尔逊博物馆兜售了一幅佛教壁画,但对其题材和绘制年代等信息并不清楚,为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史克曼在打听到它有可能出自山西洪洞的广胜寺后,于1934年专门前往山西,找到了记录着出售始末的石碑,确认该壁画来自广胜寺下寺大殿的东壁,绘于元代,内容为“炽盛光佛佛会”。
1934年,博物馆又买入一尊金代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运回美国后,在史克曼的匠心设计下,被陈列在一间中国展厅的正中,《炽盛光佛佛会》壁画位于其后,明代楠木藻井置于其上,通过一种类似“中国庙宇”的情境重建,使那些没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也能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故一直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天。

1931年初,史克曼访问龙门石窟宾阳洞时,《帝后礼佛图》浮雕还没有被破坏,他对其进行了拍照并制作了拓片。年底,史克曼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看到浮雕的碎片后,告知中国古物保护委员会,得到他们将采取措施、阻止破坏的答复。遗憾的是,1933年,当史克曼再访龙门石窟时,《帝后礼佛图》的大部分都不见了,同行的克罗泽女士在史克曼建议下愿意出资雇用军队或警察对石窟进行保护,但遭到当地政府拒绝。1934年,三访龙门石窟时,《帝后礼佛图》已被全部盗走,以碎片的形式分散于北京、郑州、开封、上海、德国等地……史克曼把这些碎片收集到一起后,1941年,根据之前拍摄的照片和拓片将其复原,陈列在纳尔逊博物馆。
二战爆发后,史克曼返回美国,应召入伍;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史克曼重返中国,为美国空军轰炸收集情报,战火纷飞中仍不忘收购中国文物。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借在北京收缴日本最高指挥部情报档案的机会,史克曼购入文征明的《古木寒泉图轴》等一批重要的明代绘画。
冷战的日子里,史克曼遇到了《西园雅集图》(春游赋诗)。早在1931年协助华尔纳工作时,史克曼就曾推荐过该图,但被华尔纳否决。1963年,史克曼在纽约路过麦迪逊大街时,偶然间看见此画正陈列在帕克-伯内特拍卖行的橱窗中,史克曼得以用“微不足道”的价格买到此画,感慨说:“我找的东西在找我。”
回归原初之幕:
李 雪 曼 “慧 眼” 与 “直 觉”
二战后,一些在太平洋地区服过兵役的美国士兵,在日本加入了盟军最高司令部公民信息和教育科艺术与古迹处(简称“盟军艺术与古迹处”),负责抢救和返还艺术珍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史克曼、普鲁默、李雪曼为代表——后来成为新一代的博物馆研究员和学者,对美国收藏、研究和出售博物馆等级的中国艺术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国共内战结束后,当新中国的建立使艺术品买卖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时,在美国,中西部的博物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使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东海岸博物馆遭到挑战。其中,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克利夫兰博物馆)及其东方部主任李雪曼成为这场浪潮的先行者和主力军。

1949年之前,克利夫兰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来自上文提及的一些藏家的捐赠和古董商的买卖。如1914年从纽约德籍古玩商埃德加·沃奇购入的东魏一佛二菩萨石刻造像碑;1915年企业家伍斯特·沃纳捐赠的北齐大理石阿弥陀佛坐像,其基座铭刻有唐房玄龄为次子和儿媳高阳公主所作(647年)的字样;1915年,弗利尔为给克利夫兰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范例,赠送了15张包括山水、人物、建筑、花卉、禽鸟和肖像等题材在内的宋元明清画作,激励他们继续收藏中国绘画;1915年从福开森处购入18张古画,其中元代罗稚川《溪桥策仗图》为端方旧藏;1919年购自纽约山中商社的(传)元代罗稚川《携琴访友图》;1921年卢芹斋赠送的安阳修定寺塔唐代舞人砖雕;1930年购自柏林的(传)南宋陈居中《胡骑秋猎图》,1933年购自纽约山中商会的南宋米友仁《云山图》,1938年购自纽约山中商会的战国蛇座凤鸟漆木彩绘鼓架等。

1952年,李雪曼任职克利夫兰东方部主任,以其坚实可靠的艺术鉴赏力,在克利夫兰建成供奉亚洲艺术的神龛,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博物馆收藏转向的典型例证,“无人能出其右”。
1929年,在时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馆馆长华尔纳的推荐下,普鲁默成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助教。在多次前往中国乡村的探索之旅中,普鲁默发现了建州窑址,发现报告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东亚杂志》和《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返回美国后,1952年担任克利夫兰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58年升任馆长。
李雪曼属于那种“为数极少的不依靠语言能力鉴赏亚洲艺术史的非亚洲人。他不会阅读中文,然而,在无法阅读题跋或印章的情况下,李雪曼能讲出石涛和张大千的区别,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史学家。他的鉴定秘诀,是他称之为与生俱来的一双慧眼以及经过精雕细琢的直觉。”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李雪曼,遇见了一个“能以真正中国的标准发出鉴赏声音”的助手——何惠鉴。

何惠鉴,广东中山人,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师从陈寅恪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1950年赴美求学于哈佛大学,师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本杰明·罗兰教授学习西方艺术史,以及哈佛燕京学社陈观胜教授进行佛教研究;1953年,获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学系和艺术史系中国历史和亚洲艺术联合硕士学位,1959年起在克利夫兰博物馆任职,凭借着对中国古典文献、诗歌、戏剧和通俗文学的掌握,在面对佛经和破译那些晦涩难懂的题字、铭文、款识方面,与李雪曼形成有力的互补,组成高效的二人团队。
1980年,李雪曼、史克曼、何惠鉴从纳尔逊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精选出300幅绘画,联合举办了“八代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绘画”展览。

尾声:
太平洋,看穿一切、眼角含泪的眼睛
在《远东艺术史》一书中,李雪曼这样说:在此重申,宽广的视野,尤其是对艺术风格的见多识广,对于鉴赏东方艺术至关重要。那与西方艺术鉴赏并无两样。在我看来,东亚艺术似乎更易理解,更有共鸣,更加人性……我们有成千上万意味深长和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它们属于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让它们成为文献学者、梵文学家或所谓禅宗佛教徒的专属领地,我们应该置身其中。东亚艺术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对我们有何意义?对它们的制造者有何意义?对东亚艺术进行整体研究,需要对那些问题给予适当解答。
当一切似乎又回到起点时,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年后,1973年,李雪曼率领北美12人代表团访华,李雪曼一行对中国的访问为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扫清了道路。当展览巡展至华盛顿时,开幕活动既热闹,又“把握了分寸”:热闹,是因为文物打破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与西方世界数十年的隔阂;分寸,则是因为文物再次在东西之间承受起外在力量的掣肘,纳尔逊博物馆的武丽生曾记述说: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展览图录和展品说明牌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审查。中国人希望展览图录中只出现文物的照片,于是,我们决定用高质量图片,印出一本好“画书”,同时安排出好的展览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