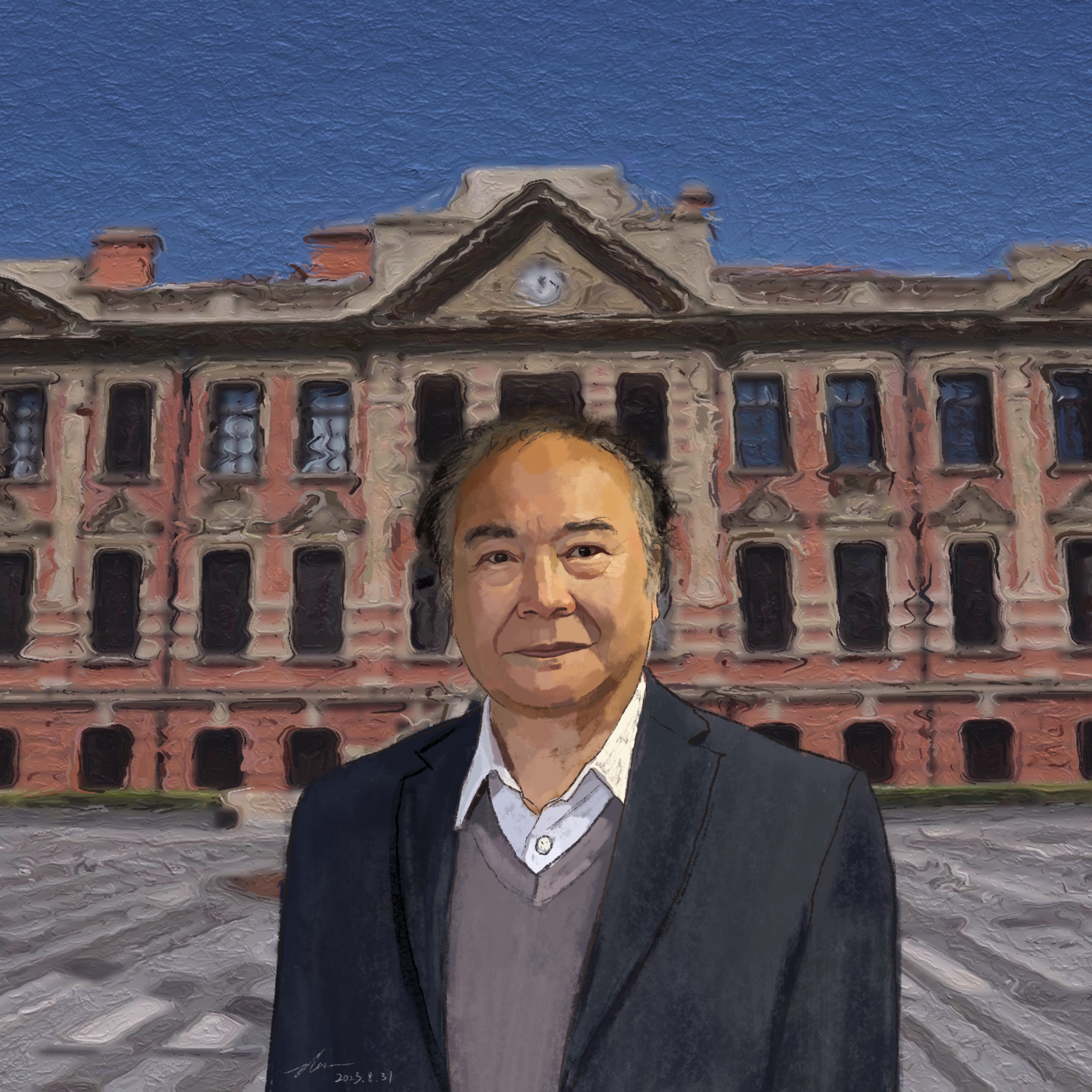
陈忠平(章静 绘)
现任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陈忠平教授曾在南京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学位,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他将研究视角从明清江南市镇转向中国近代商会,201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Modern China's Network Revolutio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近期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中译本《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近期,陈忠平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谈了清末商会的起源,以及商会这一“革命性”组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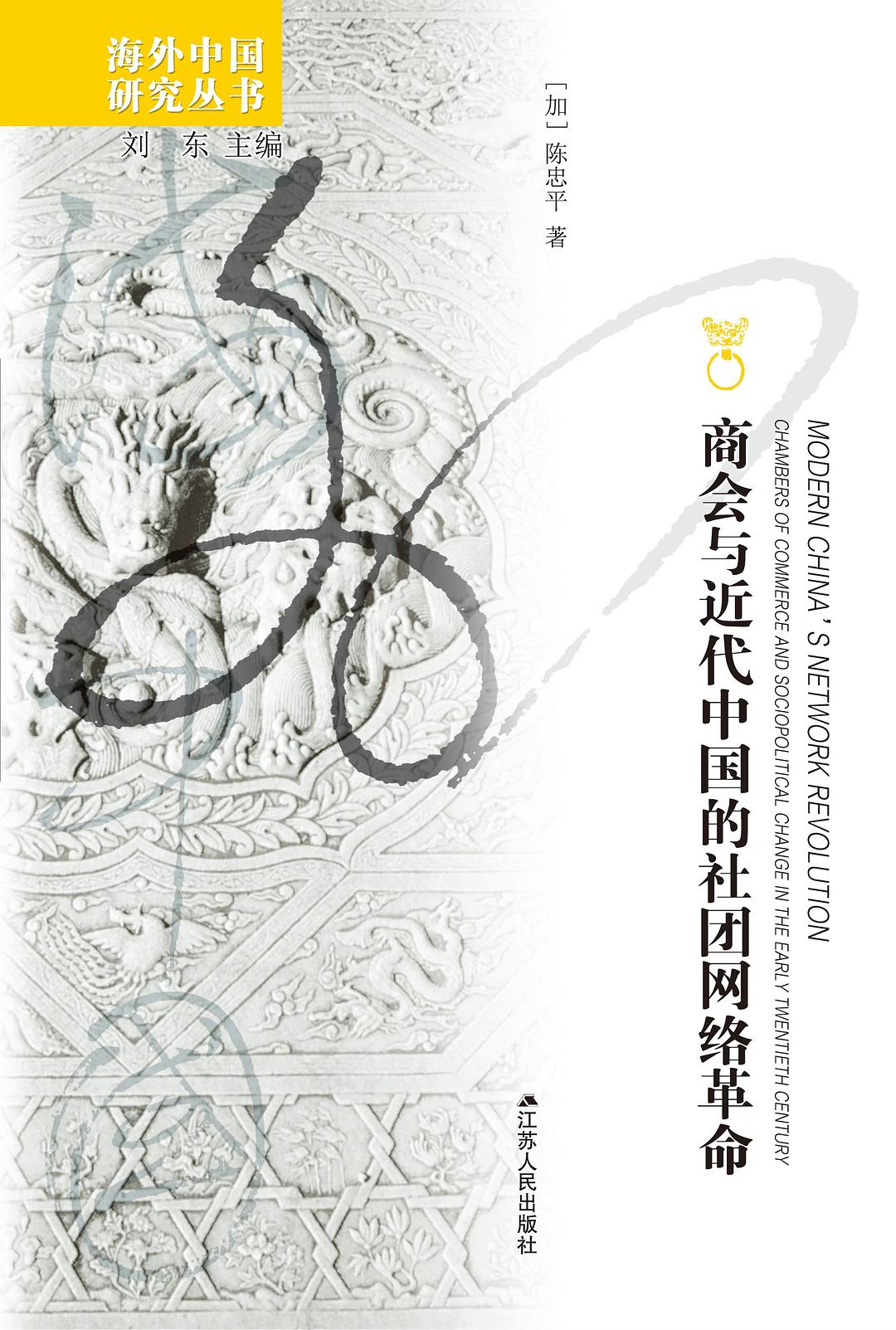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
中国历史学家对近代商会、商团的研究似乎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这与那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比之前大幅度放松有关。具体到个人,我知道您的博士论文就是围绕商人、商会展开的,您是什么时候对商人这一群体产生兴趣的?
陈忠平:我很早就对商人研究感兴趣,我是南京大学历史系1977届的本科生、1982-1984年间的硕士生,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明清经济史,就涉及商人。只是国内的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时段到鸦片战争为止,而不到清末,所以我在国内基本上研究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也包括商人,写过一些商人的文章,比如徽商,还有广东、福建商人的活动。
这本书跟我在国内做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第一,它不是国内学者所研究的明清经济史,它在国内史学界属于近代史;第二,国内的历史学界主要是做实证研究,就是搜集、研究原始资料,而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在近代中国商会怎么形成网络,又怎么带动其他社团网络发展,造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这涉及了整个中国。
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研究之间有一个很大区别,这也是我当年读博士时感到很痛苦的地方。
我在1990年出国以前,已经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而且在1987年得到了教育部最早设立的青年社会科学基金——当年全国第一批只有十五个人。我在国内接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搜集和分析原始资料。我的硕士导师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叫洪焕春,是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虽然是南京大学的名教授,但他甚至连学士学位都没有,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外祖父孙诒让是清末儒学大家,是温州瑞安的首任商务分会总理,也是浙江教育总会的副会长。洪焕春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孙怡让的儿子孙延钊学习。孙延钊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担任过温州市和浙江省图书馆的馆长。所以,我导师就是由他的舅舅把他带进图书馆,在图书馆里自学成才的。他自己看书,自己写历史文章,慢慢地小有名气,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就聘他去当助理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和一部分教学人员就归到南京大学。在他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经济结构研究。这个选题受到当时费孝通等学者研究小城镇风气的影响。我的导师要求我在写论文前一定要把所有的相关原始资料全部看完,争取在论文写完五十年之内没有任何人能发现一件新材料来挑战我的研究。这是他对我的要求。所以我当年所参考的原始资料中仅地方志部分就从江浙的省志、府志、县志、镇志查到村志,后来在国内发表的中文文章基本上就是以这些原始资料为基础的。
我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把二十多篇中文论文送给导师Harry J. Lamley,中文名字叫蓝厚里,他一开始吃了一惊,说我都可以当他的导师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像我发表那么多文章,当时国内发表文章相对不是太严格啊。对于我要写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的博士论文,他给我的建议和我的硕士导师完全不同。他说:第一,你根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中文、英文和日文的相关原始资料;第二,即使穷尽这些原始资料,把它们全放进博士论文也不是好论文。他说西方的论文最重要的是有new ideas,就是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看法。西方的历史研究需要在史料分析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出来。在我出国之前,国内的论文和著作基本上没有结论部分,讲完与论著有关的历史故事就完成了。如果说中国历史学家基本上就是用史料讲故事,西方人更注重的是故事背后的含义。
我为什么选商会这个题目作博士论文呢?实际上我当年还是想继续做我在国内就开始的江南小城镇研究,因为有关材料也很多。但是,当年费正清先生的高足——刘广京在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正好给我上一门研究生课,他建议我做近代商会。我原来在国内是研究明清史的,当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不是太熟悉。但他这么一跟我说,我就觉得是个好题目。一方面我过去对明清商人做过研究,另一方面就是商会的史料,比如章开沅等先生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等资料已经出版了。1991年一个辛亥革命纪念会议在檀香山召开,几乎全世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都去了,我正好负责接待章先生,他也给我很多鼓励和帮助。所以,这个选题实际上有点偶然性。
您在研究晚清长江下游商会的兴起时,重点讨论了上海西方人创办的商会如何成为中国商人的模仿对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中国商会的建立与运行受到国外影响较大,这种影响在哪些方面令您印象深刻?
陈忠平:关于商会起源的说法很多。在比较传统的说法中,像日本学者强调商会就是由同乡同业的行会发展而来,所以他们认为商会就是超级行会。这好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各行各业和不同地方来的商人联合起来,不就成了一个城市的商会了嘛。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江南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即从某一地方来的商人同乡会馆或他们专门的行业公所从县、府到省级或从单一到多种行业联合起来,更不要说这些同乡同业行会能够在某一城市联合起来。
第二个说法就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形成了商会。实际上,即使在上海这种最为现代化的都市,如果把资产阶级定义为与近现代工商业有关的商人,他们在当地的清末商会中也从来没超过一半会员。我研究的1902到1911年间江浙的商会有二百一十个,其中将近百分之五十是在县城以下的市镇一级,这些地方当年根本就没有什么近现代工商业,你怎么说他是资产阶级?
另外有西方学者提出近代中国商会是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精英为了社会的复兴和稳定动员起来,然后形成的一种组织。但是问题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到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差不多五十年。清末社会精英动员了五十年怎么也没出现商会,突然1901年以后就大规模出现了?从1902年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名义出现的第一个商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际,江浙地区一下就出现了两百多个商会,全国有一千多个,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清朝政府为了控制商人和商业,所以从1902年之后大办商会,这也说不通。江浙地区有二百一十个商会,百分之五十在市镇一级。清代最低层的政府机构是在县一级,江南那些大镇有一些县丞,就相当于现在的副县级,但数量很少,大概只有十几个镇有这种官员。那怎么解释一百多个市镇的商人自己办个商会,主动让政府控制?
我认为这种组织是清末的社会精英,特别是商人精英,对国家危机、尤其是西方入侵的一种反应,也是他们与清政府互动的结果。因为清末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社会与民族危机,所以他们把西方商会不光作为一个模式,也是想用这种西式组织来抵抗西方,振兴中国经济和商业,也振兴整个民族,有民族主义反应在里面。就像当年郑观应说的,要用商会领导中国进行一场商战。但是,他们最早对西方商会的理解有很大错误。在中文里面,最早使用“商会”这个词的人之一是郭嵩焘,就是中国派到英国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说什么是商会?商会就是把商人联合起来的组织。所以商会就是要把中国商人联合起来,对付外国人经济侵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公车上书里说西方人为什么能够在亚洲建立殖民地,他们在印度靠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靠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对的,但他说这些公司就是商会,我们中国人就要办这种商会。他后来在海外办保皇党,也叫公司或者商会,说明他实际上对于西方商会和公司的关系是有误解的。
我觉得对于江南地区商人精英的最直接的刺激还是西方人在上海办的一个商会——西人商务总会,它最后集聚了大概十多个西方国家的公司,也包括日本公司。它联合西方政治势力,在外交上和西方官员联合行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这对华人刺激很深,但是,中国的商会绝对不仅仅是模仿西方商会。
您和不少学者都提到,清末商会标志着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法人社团的首度出现。1904年,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非政府组织。那这些组织和此前传统的商业组织如行会,还有一些地缘组织,以及1895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改良和学术组织最大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陈忠平:公所这种同业的组织实际上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正式的同乡会馆在明初出现于北京,是安徽芜湖籍的官员最早在北京办的,以便同乡官员互相照顾,后来商人也模仿,使用会馆这个名字。至于学会,比如明末就有东林党,就是文人士大夫围绕东林书院形成的一个组织。明代灭亡以后,清朝皇帝如康熙认为明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党争,所以就禁止了,不允许士人结社。甲午之后康有为等开始倡导办学会,比如强学会。但是所有这些组织跟商会相比有两大区别:一是商会以前的组织从来没有得到正式的法律承认。过去比如宋代皇帝可能欣赏范仲淹,支持他办一个范氏宗族组织,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法律保证这个组织是合法的。同乡会馆取得政府支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同乡官员取得庇护,也并没有法律保护。清末学会也是这样,你看康有为在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很快就被禁止了。为什么能办?是因为张之洞这些官员一开始支持他。为什么又停掉了,因为没有法律保护,其他人一反对可能就完了。

盛宣怀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
商会1902年出现于上海,首先是由盛宣怀上报,清朝中央政府批准的。因为盛宣怀当年跟外国使节进行谈判,需要商人提供信息和其他帮助。到1904年又有关于商会的法律颁布,因此商会成了最早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组织。之后像教育会、农会,就连后来一些合法政党,实际上它们的起源就是从商会开始的。中国近代所有的民间组织合法性实际上是从商会开始得到的。
另一方面,此前中国类似组织的网络从来没有像商会这样普及。比如说一个同宗组织,跨地区、跨省甚至跨国都可以,看起来它的网络也非常广阔,但问题是你不是那个姓的人就进不去。实际上很多宗族组织也不是所有同姓的人都能进,还要看是否来自一个小的地方。同乡会也是这样,你不是同乡肯定进不去,而且这些组织在不同地区散布,稀稀落落的,有了同乡、同姓成员了才能办,没有就不可能。而商会建立组织之后发展的网络却是普遍的,从省到县、乡镇。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能对商会而言最重要,一是法人社团,第二点是普遍的商会网络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在商会以前达到这两步。
您在书中提到,这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革不仅类似、而且超越了池上英子(Eiko Ikegami)所指出的“德川时代网络革命”,即在日本史上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网络的突然扩展。这方面您有何理解?
陈忠平:池上英子这本书叫《文明的纽带》,描述了近代日本通过新的文化交流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比如新的出版物、茶道等文化方面交流的新发展,促使日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不过她的研究局限于文化方面,主要聚焦在社会文化交流方面,而我研究的网络主要是在社会政治方面,商会不光是通过新式组织制度把商人联结起来,实际上也把其他不同的社会各界精英联结了起来。当年参加商会的人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仅仅从事商业的人。根据清朝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法律规定,从事工商业的人,包括信贷、银行等行业都算商人,甚至得到过状元头衔的张謇也经商,还有官员退休从商的,他们是真正有影响有势力的绅商。商会的领导主要是这些既有工商业财产,又有社会影响和政治关系的人物。有意思的是,商会成立的时候,有好多并非商人,可能是教育界人士或地方士绅,也参加了商会。所以,商会是把不同的社会精英联系了起来,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把整个社会、起码说地方社会联系了起来。
中国近代的政治领袖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中国人组织起来,为了一个政治目标奋斗。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生存,需要挽救国家危机,首先要将国民联合起来。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到同盟会和国民党,实际上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把中国人的力量通过这种组织凝聚起来。据周锡瑞等西方学者研究,孙中山并不是辛亥革命实际领导人,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还在美国。根据我今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新书的研究,他在民国初年反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政治军事运动中起的作用也不重要。为什么孙中山最后成功击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手,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他在组织、控制政党方面所做的努力,就是怎么把他的组织网络制度化,变得越来越坚强有力。我这本关于商会的书在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关注商会起源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关注商会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联系和整合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的组织网络才能把中国人联合起来。近代商会从这一点上说,是一个先锋,我说的“网络革命”,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商会建立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因此有了更大的力量。不过在您看来,清末商人更大的力量在于通过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商会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网络,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精英权力关系甚至整个社会结构。这是相当有意思和大胆的判断,您能否具体谈一下,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陈忠平:社会网络并不是近代中国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尤其中国人讲关系,人际网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关于商会的研究最早也没有使用网络理论,因为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搞一套理论出来,我导师当年对新的理论也相当谨慎。所以,我那时主要使用一种传统的组织分析,用商会去做组织分析,这是很正常的选择,当时国内学者比如朱英、马敏等关于苏州商会的研究就是这么做的。后来之所以转向网络研究,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是一个很巧的事情。2000年香港大学召开一次学术会议,题目是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近代中国商人、商会与商业网络之间的关系,启发我想到怎么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因为用组织分析来研究两百多个商会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个一个去分析不可能,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很严密的系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转向网络研究,但是网络一直被用来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中国人际关系很好奇,用同乡、同学、同事这种个人关系来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包括党史。但总的来说,西方人把这种中国的人际关系看成一种负面现象。
网络分析在西方至少有五十年的历史,但是他们主要是谈个人关系,较少谈整个组织。但我觉得很难把个人关系跟组织化制度化关系分开来。个人关系是从哪来的?近现代社会的个人关系主要是因为你在一个组织,比如大学、公司,大家聚到一起形成的,你怎么能把个人关系跟组织化关系分开来?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原来网络研究中把个人关系和组织关系分开来的方法,把个人关系的网络分析融化到组织制度化关系的研究中,而且我认为组织制度化的关系可以改造个人关系,它比个人关系发展得更广阔,可以超越个人关系。
清末商会网络革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制度化,就是从个人层面开始,关系变得正式和组织化;二、关系扩大化,网络的生命力在于扩大,当然网络也会萎缩、衰落,那就会失去活力;另外两个方面,我特别强调的是它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网络成员的互动增强。网络能够把不同的人和组织汇聚起来进行互动,而且还跟其他社会力量进行互动,所以我觉得历史真正发展的动力是互动的力量。商会主要是商人精英的组织,但可以通过他们把普通商人拉进它的网络。当年的商会组织网络很巧妙,比如清末上海商务总会规定有三种会员制度、四种会友制度,普通商人不是正式会员,但可以是会友。从这一点上说,它不光联系了工商界,也联系了地方社会,甚至联系了整个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根本性的革命性变化。

苏州河畔的百年建筑——上海总商会
清廷支持商会和商人群体在新政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振兴经济,扭转国家命运。但北京从一开始就对商人群体保持警惕,带有控制的意图,比如曾经想对商会分而治之,但效果很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为什么?人们注意到,一些商会后来居然可以组建武装力量(商团),甚至可以举行军事演习(如上海商团公会1910年在浙江北部进行过军事演习),而这一切又是在官方许可之下的,对此您如何解释?
陈忠平:这要从更大的角度来说。商会的出现反映了整个社会力量的兴起,当年清政府想以传统的方式来控制这个力量,但后来发现已经不可能。另外一个方面,清朝中央和省及府县地方政府都想控制商会,导致了官方之间互相斗争。中央政府为了绕过省及府县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商会,给了商会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比如规定各地商务总会给省级总督、巡抚用“呈”这种形式递交文件,但督抚以下可以用“移”的形式传递文件,等于平级。这个地位很高,意味着地方商会不是地方官员的僚属,他们不可以去直接控制,这给商会造成了一个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势力。第三就是在清末,清政府内外交困,是政府权力比较软弱的一个时期,有好多方面需要商会帮忙,所以只好给商会权利,商团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清政府一开始也不想让商团有武装,但商团强调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东亚病夫,需要通过体育来振兴体格,这个理由光明正大,政府没有办法干预。另外,中国的警察制度到1905年才从西方引进,社会治安管不了。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禁鸦片令,很大程度上是靠商会控制的商团帮忙实行。上海的鸦片烟馆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鸦片烟馆和赌场又都连在一起,这些人要暴乱的话,清朝地方政府官员也没力量,因为他们手上也只有那几个兵,所以上海商团最早有武装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其实一直到清朝末年,浙江省政府都不让办商团、不让商会的成员进行武装训练,但是最后没办法维持治安,只好听之任之。
很多商人精英在清末最后几年加入了各地的咨议局,他们通过地方议会和自治机构变成了新的政治精英。我注意到您以商会网络的角度解释或强调了商人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众所周知,上海商团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座城市的独立暴动。
陈忠平:商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大部分中外学者是讨论它们怎么与清政府产生对立,发生矛盾,所以转向革命。商会领袖等改良派人物和清朝政府为了提前召开国会,还有铁路等问题确实有冲突,不过如果将商会和清政府也放到社会政治网络里去分析,就不能光讨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互动。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合作、谈判、妥协等形式的互动。实际上商会与政府发生冲突,也是他们在新政中的合作造成的。商会实际上是帮助推动了清政府的改革越来越激化,从这点上说来,他们是和清朝政府合作的,然后才有了矛盾,辛亥革命无非是把双方之间从合作到冲突的互动放大了、强化了。上海商会领袖帮助革命党领导的反清起义,打下江南制造总局。但是在苏州他们又跟江苏巡抚一起宣布和平独立,实际上也是跟清朝前官员合作。无论是与清政府冲突、与前清官员合作或其他形式互动,都帮助了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所以不能说商会是所谓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组织,实际上他们在辛亥革命中还是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的。
正如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中所说,商人成了辛亥革命后新政权的第一个牺牲品,共和政体之下的商人组织似乎应该更加牢固、更有力量,但他们为什么没能阻止新的专制人物,甚至,1912年商会代表都没能进入国会?
陈忠平:我觉得这还是要从中国整个近代史的趋势来看。因为近代中国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 所有中国人都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把中国人团结起来,然后让国家富强。当年商会领导人物也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当然曾经寄希望于革命党人,不过很快发生矛盾,比如上海革命党领袖陈其美没钱了,就绑架、软禁商会领导人。孙中山一到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就要江浙商会出几十万大洋。另外商会的领导人从革命党人身上并没看到能够统一中国的希望, 他们就转向袁世凯,还是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从中国近代的长期趋势看,为什么在革命之后连续发生新的革命,包括辛亥革命之后的大革命(国民革命)以及后面的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是中国人希望一个新的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把中国人的力量凝聚起来,统一国家,实现富强,这是个总的趋势,包括商会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成为民国初期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孙中山
清末中国商会的社会功能被认为超越了西方的同类组织,具备很大的政治能量,但也有学者认为,商人参政仅是一个短暂的权宜之计。从经典的社会-政府关系看,是否可以把商会在清末的兴起看成对弱政府的回应?
陈忠平:我关于商会的书里也提到了这种学术观点。确实,清末政府力量的衰落给商会发展、组织网络甚至武装力量提供了机会。不过商会的网络经过制度化发展,即使在强政府下也已不可逆转,法律层面的社团网络在中国近代政治当中的作用从来没有消失,这才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社会政治变化。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和国民党时期,中央政府强了,社会力量就被压下去了,但是社团组织的制度化网络基础还在。比如说,袁世凯到1913年的时候军事独裁力量很大,他后来把国会、地方议会解散了,也解散了国民党。但是在袁世凯力量最强的时候,商会与它进行了斗争。当时袁世凯企图通过一个《商会法》,取消总商会和商务分会这种名称,从而取消商会的网络,分而治之。但最后商会抵制成功了,迫使袁世凯取消原有计划,采用他们要求的《商会法》。近代社会和传统帝国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关系毕竟有很大的区别,帝国制度之下皇帝可以说是天子,享有天命来统治天下。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在哪?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商会等社团的支持和认可。所以袁世凯不仅没有把商会解散,还依赖商会的支持来称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中国也是政治制度上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国民党时期也是一样,尽管国民政府想改组商会,也不能把它们全部去掉。
您在书里说了,资料截止到2009年,现在推出的中文版距此已过去十几年了。如果现在重写这个题目,您会在哪些方面做一些补充?或者说现在看这本书有什么遗憾之处?
陈忠平:这本书让我现在重写,也不见得能写得更好,而且我也没有发现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有重大缺陷。要说遗憾,有一点是当时局限于国内的研究,主要呈现的还是江浙商会。实际上,商会的研究空间还可以再扩展到跨国层面,因为近代中国商会在海外也有一定发展,在温哥华、新加坡的华人商会都可以纳入。我的书里涉及了一些跨国的内容,比如说江浙商会跟美国商会的合作,特别是上海商务总会在1905年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个全球性华人运动,我的书里面对此有所讨论,但不多。今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新书——Transpacific Reform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1898-1918,内容有关于康有为、孙中山领导北美华人进行的跨太平洋改良和革命运动,它弥补了我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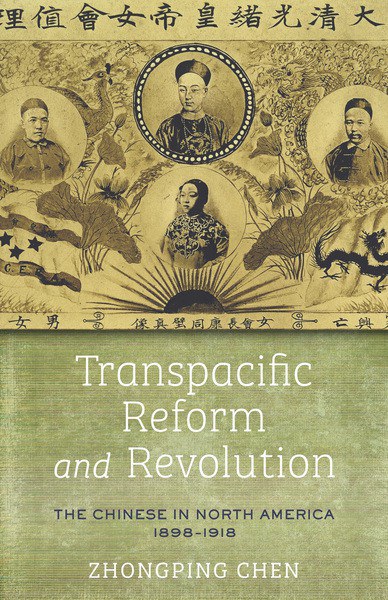
陈忠平教授新著: Transpacific Reform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1898-1918